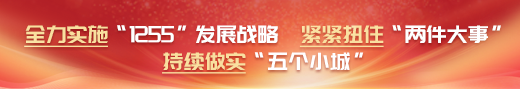高平·非遗有看头|高平纂面:千丝纂史 面礼春秋
在高平有一种面食,名字里藏着一个古老的汉字——“纂”。这并非日常书写常用字,它从《周礼》的典章制度中走来,意指一种庄重的编连、一种系统的辑录。当它与一碗面相遇,我们品尝的便不仅仅是麦粉的滋味,而是一段被巧妙“编撰”起来的地方史,一口穿越千年的文化鼎鼐之味。



大周村位于高平市区西南,隶属于马村镇,毗邻高平关。大周村建村历史悠久,据传:早在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,北周柱国大将军杨纂镇守高平关,官兵家属遂在离关不远一处靠山临河的平川建村而居,起名“周纂镇”。杨纂是河北涿鹿人,他足智多谋、能征善战,爱兵如子、治理有方,当看到麾下将士南征北战,常因战事紧迫无暇埋锅造饭,便结合山西面食揉、擀、把、饧等工艺,在面粉中按一定比例加入盐和碱,创造出一种耐存放、易携带、方便烹饪的面食。这种面食煮制快捷,劲道十足,深受士兵喜爱。后来,为了纪念杨纂创造之功,人们把这种面叫作“纂面”。为地方风味饮食找一个名人背书,这是饮食文化中常见的做法。但纂面背后的故事却远远不是如此简单。




考古发掘中,我国先后从新疆、甘肃、安徽等地发现了距今4000—3000年的碳化小麦实物,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“麥”字。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小麦多煮成麦粒饭食用,由于小麦面筋含量较高、口感差,人们并不喜欢食用,文学中常用“麦饭豆羹”“麦饭疏食”来形容生活的艰辛。汉代以后,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石磨的普及使用、面食的发明,民众对小麦的需求剧增,小麦栽培开始遍布黄淮流域,并成为北方人的主食。受制于麦种、磨具,小麦制粉工艺还比较落后,往往质粗、多麸、质地不均匀,导致无法加工面条。汉代时麦粉是捏饼煮食的,这就是典籍中的“煮饼”。唐代开始出现了面条,宋代时才广泛食用。



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,人们无意中发现添加草木灰可以增强面粉的筋性。北宋文人庄绰在《鸡肋篇》上卷里曾写到:“陕西沿边地苦寒,种麦周岁始熟,以故粘齿不可食。如熙州斤面,则以掬灰和之,方能捍(擀)切。”这说明蓬灰至迟在宋代已经使用,后来则进化为添加草木灰泡水澄清得到的碱水。这一做法在兰州牛肉面以及南方多见的碱水面中还能看到影子。兰州多戈壁滩,人们用盐碱滩上生长的碱蓬烧灰,得到土制的碳酸钠、碳酸钾,最初用于清洗衣物、头发,后来也许无意中用于和面,发现能使面条柔韧筋道、易于擀切,于是广泛使用。南方的碱水面最初写作“枧水面”,制法与兰州的蓬灰相同。

与泽州大阳的“馔面”相比,大周纂面在“韧”与“爽”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。大阳馔面或许更显宫廷“馔玉”之风,造型更为讲究;河西碱面则以其明确的碱香和独特的黄亮色泽,透露出应对水土、改良口感的智慧。做面食“盐是骨、碱是筋”,这句话堪称一千多年面条制作史的经验之谈。如果说卤水成就了豆腐,盐和碱作为两种最普通最常见的“改良剂”,也成就了面条的百绕千回。“筋、骨”二字明白无疑地指明了它们的功能作用:盐主要用来增加面条的强度与硬度,碱主要用于改善面条的延展性和韧性。从实践中看,加碱可以显著提高拉面条的质量和效率,而对延展性并无特别需求的非拉面类面食,如刀削面、手擀面等,使用普通面粉,加上合适的揉面饧面过程,不加碱面也能做出口感合适的面条。纂面三兄弟都是擀面类,理论上加碱并不是必需,那为何这样的做法会流传至今呢?有人认为是碱面有特殊的香味,但真正的奥妙则隐藏在经济背景当中。

纂面三兄弟地域位置相近,都在泽州与高平交界,地处官道、商道之上,或者毗邻冶炼等产业中心,是人流密集之地。人多好干活,但吃饭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,尤其在工业化之前,在短时间内满足工坊工匠、过路客商的用餐问题,对餐饮业的发展提出了苛刻要求。提前擀好的面条会发酵变酸,也会发软变坨,加入碱后,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纂面做好以后可以放两三天,一方面是便于散碱,但同时也延长了保存时间,面馆就有了短时间内供应大量面条的可能。此外,面条擀切好后,要撒上面粉防止粘连,这就导致面汤很快就会变得浓稠。面馆在中午一个时辰内往往要煮上百碗甚至更大量的面条,那就需要十几分钟换一次水重新烧开,这不仅会浪费燃料、水,耗费的时间成本也是餐饮业者不能忍受的,这将耽误多少生意?从饮食习惯来讲,无论南北,都喜欢面条要爽利,面在锅内煮熟的过程中也是不能浑汤的。碱水面正符合要求,耐煮、耐泡,即便泡瘫了也不会产生大量游离淀粉,不会浑汤。所以,即便在广泛使用煤炭的山西,还遗留下了纂面这样的碱水面并不是偶然,而是经济、商业发展的需要。

在大周,纂面绝非寻常果腹之物。它还是婚丧嫁娶、节庆寿诞等重大礼仪场合当之无愧的主角。宴席上,一碗热腾腾的纂面端上来,往往意味着仪式进入了最核心的阶段。这长长的、不断的面条,寄托着人们对生命绵长、家族昌隆的美好祈愿。它连接着宾客,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,如同一条情感的纽带,将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,“纂”入家族、社群的宏大叙事之中。这方土地上的孩子们在一次次宴席中不仅记住了纂面独特的口感,更无形中习得了背后的人情世故。于是,大周纂面也超越了食物本身。它是一根有生命的线,一头牵着千年的农耕文化,一头系着今日的烟火人间。

当你看过了大周的古建筑群,坐在村里一间餐馆的古旧餐桌前,面对那一碗什锦卤子中根根分明的面条,不妨细品:那舌尖跃动的,是太行山的风与光;那齿间纠缠的,是高平关的筋与骨;这一碗,是岁月的编纂,是生命的续章。(中共高平市委党校)
本页二维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