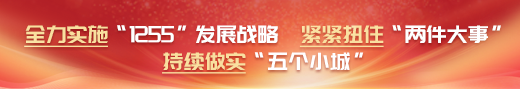袁致和:点燃高平革命的第一簇火苗
高平,作为太行太岳革命老区,红色文化底蕴深厚,众多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其中,袁致和播撒革命种子、创建党组织的事迹,犹如黑暗里的一簇火苗,至今仍闪耀着炽热的光芒。
麻油灯下:刺破黑暗的冬夜微光
1926年腊月,晋东南的黄土高原上,凛冽的北风正呼呼地吹过长平大地。瓦窑头村的一间土坯房里,麻油灯芯摇曳,映着七八张年轻的面庞。灯影中央,袁致和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袍,身形清瘦,却目光如炬,对着周围的人说道:“苏联的工人农民都站起来了,咱们中国的穷苦人,也得抱团儿闹革命,把那些骑在咱们脖子上的官绅掀下去!”他的声音不高,却像一道惊雷,在每个人的心海深处炸响。
这一年,他22岁,刚从长治四中返乡。在长治求学时,他第一次读到《新青年》,第一次听说“十月革命”,那些关于平等与解放的火种,早已在他心底燎原。1926年春,在太原地委委员周玉麟的引领下,他面对党旗庄严宣誓,成为高平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。此刻,他受组织委托回乡建党,这间破旧的土坯房,成了高平革命的第一座熔炉。
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村小学教师袁凤鸣。这个戴着断腿眼镜的年轻人,平日教娃娃念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时,总是把戒尺拍得震天响。袁致和将《向导》周报塞进他的手里,低声说道:“凤鸣哥,共产党就是要铲平这‘朱门’与‘冻死骨’的路,给咱穷人踏出一条阳关大道!”袁凤鸣镜片后的眼睛亮了,他紧紧握住袁致和的手,激动地说道:“致和,我跟你干!”
随后加入的李子修是个黑脸庄稼汉,听袁致和讲了“剩余价值”后,他猛地一拍大腿,说道:“这么一说,咱不是命贱,是叫人家当牛马使了!这账得算!”三人常聚在油灯下学习、争论、唱《国际歌》。李子修嗓门大,唱到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”时,总惊得袁凤鸣忙捂他的嘴。
1927年1月,袁致和见时机成熟,根据太原地委发展党员的规定,介绍袁凤鸣和李子修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立高平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高平特别支部,简称高平特支,袁致和任书记,成员有袁凤鸣、李子修,直属中共太原地委领导,成为全省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。
三双年轻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像三棵倔强的幼苗,誓要顶开压在高平人民头上的冻土。
瑞云观前:怒潮奔涌的苍龙觉醒
高平特支成立后,袁致和紧接着着手筹备瓦窑头农民协会。成立当天,农家院落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乡亲——有拄着拐杖的老人,有怀里抱着娃娃的妇女,还有肩上还扛着锄头的壮汉。他们目光灼灼,齐齐望向站在石碾上的袁致和。只听袁致和对着乡亲们大声喊道:“乡亲们!农民协会是咱穷人自己的组织,以后谁再敢欺负咱,咱就跟他干!土豪劣绅欺负咱,咱就革土豪劣绅的命!”
话音刚落,一位豁牙老汉激动地举起烟袋锅,高声应和道:“好!这世道,早该变变了!我们现在就跟着你闹革命!”
革命的矛头直指县长陈迺蓉和劣绅刘干臣。二人借“城防”之名预征三年钱粮,逼迫瓦窑头村王老汉交出耕牛,为此老伴险些自尽。袁致和闻讯,脸色铁青,一拳砸在桌上,怒吼道:“这哪里是防匪,这是要逼死咱穷人啊!”
农民协会成立后,为进一步团结进步学生,袁致和旋即又着手联系返乡学生,筹备学生联合会。
1927年2月16日,正值元宵节,瑞云观前人头攒动。高平留潞学生联合会在此召开成立大会,袁致和当选主席。只见他跃上高台,寒风掀起棉袍一角。面对台下的人群,他沉痛地诉说道:“乡亲们!陈迺蓉和刘干臣预征钱粮,逼得王老汉差点家破人亡!他们的十大罪状,条条都沾着咱穷人的血泪!”他一条一条地数着,以铁的事实控诉了以刘干臣为首的一伙劣绅,伙同贪污县长陈迺蓉,以防匪为名,设立防务局,巧立名目预征钱粮,征收苛捐杂税,为非作歹,敲诈勒索高平人民的十大罪状。每数一条,台下群众的愤怒便累积一分。“走啊,去县政府!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,人群便如决堤的洪水涌向县政府。学生领头喊口号,农会会员在两侧护卫,沿途百姓不断加入,队伍越走越长,宛如一条觉醒的苍龙。
当天下午,学生会一边向县政府递呈文书,一边在街头张贴标语,积极分子更是当街发表演讲。然而,学生们的正义之举却触怒了陈迺蓉。当晚,他便以“扰乱治安”为名,派警察扣押了邵心斋、常世禄、巩祯庆、吕建章等学生积极分子,以及开明绅士唐之恭、何桂堂。
袁致和得知消息后,连夜召集高平特支成员及学生会骨干,在瓦窑头村土坯房里紧急商议对策。李子修攥着拳头,满脸怒火地喊道:“咱跟他们拼了!”袁凤鸣忙站起来说道:“硬拼肯定不行,警察荷枪实弹守着,万一伤了人怎么办?”袁致和来回踱着步,沉默不语,忽然停下脚步,缓缓说道:“硬拼不是办法,我们得找上级支援。我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现在正好利用我的国民党员身份合法开展革命工作。之前我与省城大中学生联合总会也有过联系,现在只有去晋城发电报求助,才能让陈迺蓉释放被扣人员。”他看着众人,语气坚定,稍稍停顿一下,继续说道:“凤鸣,你留在高平,稳住农协会和学生会,防止陈迺蓉趁机打压;子修,你跟我去晋城。”
就在两人准备出发时,天空突然下起雪来,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在院子里。袁致和毅然决定连夜去晋城求援。80里山路,积雪没过脚踝,两人深一脚浅一脚,躲关卡、避盘查,赶到电报局时,浑身近乎冻僵。他颤抖着手拟下电文:“省学联钧鉴:高平县长陈迺蓉勾结劣绅刘干臣,预征钱粮,扣押请愿学生及绅士,恳请速援!高平学生联合会叩。”发完电报,他望着雪后初霁的远山,对李子修说:“革命就像这亮光,再厚的乌云也挡不住。”
等待回电期间,袁致和还担心高平这边出状况,托人给袁凤鸣捎信,让他务必看好农协会和学生会,别中了陈迺蓉的圈套。没想到,陈迺蓉真的派人去瓦窑头村散布谣言,说袁致和在晋城被抓了,被扣学生也会被判刑,借此让农协会和学生会自乱阵脚。袁凤鸣得知后,立刻召集乡亲们,拿出袁致和捎回的信,大声说道:“大家别信陈迺蓉的鬼话!致和同志已经顺利发出电报,省里很快就会给咱答复,只要咱团结一心,肯定能救出被扣的人!”乡亲们听了,这才安下心来。
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下午,省城回电了。只见上面写着:“已电令高平呈报实情,立即释放被捕人员。省学联将派代表前往。”袁致和长舒一口气,拉着李子修就往回赶。
凯歌高奏:长平破晓的胜利曙光
高平县城内,阴冷的牢房关不住追求光明的决心。被扣押的学生和绅士们,尽管身陷囹圄,却无一人退缩。他们坚信,袁致和正在为他们奔走,革命的火苗绝不会被轻易扑灭。
陈迺蓉收到省政府“彻查实情”的电报后,只想释放学生,却不愿答应学生的要求。而被扣人员得知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后,坚决不出牢房。陈迺蓉见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。他让刘干臣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地主乡绅,去县衙门口“请愿”,说学生“扰乱地方秩序”,借此为其扣押学生的罪行开脱。同时,刘干臣还偷偷给牢房看守塞钱,让他们克扣饭菜,以逼迫被捕人员在饥饿中屈服。袁致和得知此事后,再次向省学联发电报,揭穿陈刘二人的阴谋诡计。
省政府的电报再一次发来,直接斥责陈迺蓉“处置失当,激化民怨”。陈迺蓉终于慌了神,在县衙里转着圈念叨:“这可如何是好……”刘干臣凑上前低声劝道:“县长,放了吧?上面都发火了。” 陈迺蓉却猛地站定,狠狠瞪着眼说:“放了?咱们预征的钱粮怎么办!”
不久,省学联代表带着省政府指令赶到高平,一见面就把指令拍在陈迺蓉桌上,说道:“陈县长,省里的命令你敢不遵?赶紧释放被捕人员,废除预征钱粮,不然你这个县长也别当了!”陈迺蓉见省学联代表态度强硬,又得知中共太原地委也在关注此事,再也撑不住了。为了息事宁人,陈迺蓉只好去牢房“赔罪”,脸上堆着笑说:“各位,之前是误会。预征钱粮马上废除,还请你们出去。”被扣人员见部分目的已达到,又赶上学生寒假结束,才走出牢房。
被捕人员出来后,“驱陈倒刘”运动继续进行。袁致和持续向省学联控诉陈刘二人的十大罪状,要求撤职陈迺蓉,严办刘干臣。
与此同时,陈迺蓉也不甘心下台,偷偷给阎锡山写信,诬告袁致和“勾结乱党,煽动民众”,想让阎锡山下令抓捕袁致和。可阎锡山当时正忙着应对北伐军,没心思管高平的小事,只是草草回信让他“妥善处理,勿再生事”。陈迺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
3月底,阎锡山迫于各方压力,正式下令撤销陈迺蓉的县长职务。劣绅刘干臣也如过街老鼠,在群众的唾弃声中仓皇逃离。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“驱陈倒刘”运动取得彻底胜利。压在高平人民头上的巨石被掀翻了,预征钱粮的苛政被彻底废除。
瓦窑头村,王老汉牵回了失而复得的耕牛,脸上的皱纹笑开了。农会会员敲响了欢庆的铜锣,游行队伍的欢呼声在高平县城的大街小巷回荡,长平大地迎来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。
星火永传:赤子之心的无声丰碑
“驱陈倒刘”运动胜利不久,袁致和调任中共太原地委。消息传来,全村人含泪相送。袁致和站在村口,最后望了一眼瓦窑头村。薄雾似离愁般笼罩着故乡的土坯房,几缕炊烟正袅袅升起。乡亲们围在他身边,王老汉急急忙忙跑来,把几个刚出锅的窝头塞进他的背包里。袁凤鸣和李子修用力握着他的手,眼眶泛红,千言万语都堵在喉间,只化作重重的点头。
袁致和挥手告别,背影挺拔而坚定。
这一走,便是许多年。他带着对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深切向往,带着对故乡热土的无限眷恋,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汹涌的革命洪流中。
从此,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命运与时代的惊涛骇浪紧密相连。太原的铁窗、石家庄的地下战线、天津的险象环生、山西抗日前线的枪林弹雨……都成为他践行誓言的战场。他多次被捕,屡受酷刑,却始终坚贞不屈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身负重任,辗转于多个关键岗位,始终夙夜在公,勤恳付出,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光辉事业。
有人问他,历经如此多的艰险迫害,可曾有过畏惧。他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,淡然一笑,轻声答道:“看到乡亲们眼里的希望,就啥也不怕了。”1971年10月,袁致和病逝,享年67岁。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他魂牵梦萦的,依然是瓦窑头村那间土坯房,和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抗争的乡亲们。
如今,瓦窑头成了红色教育基地。1927年点燃的那簇火苗,此刻化作山村里的幸福图景,化作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壮阔蓝图;袁致和这个名字,如同一座精神的丰碑,与高平的山水融为一体。这份红色记忆,早已融入咱高平人的血脉,代代相传,成为永恒的精神力量!(田杰君)
本页二维码